禽流感阴影下的科学家:没人能在危机中置身事外

大流感阴影下的科学家

培养病毒的鸡蛋。香港大学流感中心实验室里每天都存放着几百个这样的鸡蛋,其中或许有H5N1病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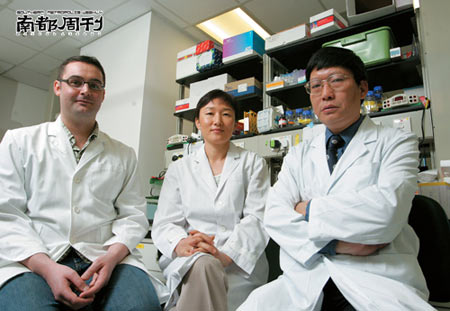
管轶与他的两个助手Gavin Smith、张锦霞。
140万人丧生,33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什么样的灾难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答案或许是禽流感。这是澳大利亚科学家对禽流感疫情在全球蔓延及可能造成损失所作的一项预测。而预测却说,这还不算是最严重的疫情。自2003年迄今,禽流感已在全球45个国家中肆虐,H5N1病毒的迅速变异,使这种原来只会在禽鸟间传播的病毒,不仅开始在猫、狗等动物间跳跃传播,更传染给了人类。195名人禽流感患者中,已有过半数不治身亡。
科学家们隐隐然听到了大灾难的脚步声。
他们警告说,如果突破某个关卡,禽流感病毒具备了人际间传播的能力,势必会出现流感大流行。根据模拟,其冲击远远超过了SARS。民众对这种可怕的病毒显然知之甚少。H5N1病毒从哪来?如何变异?谁是它传播的罪魁祸首?
2006年4月,一个越冬鸟开始北迁的季节。
禽流感也许会再次藉着候鸟的全球性迁徙而蔓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这场抗击禽流感的战役中置身事外。
中国香港
寻找H5N1族裔
科学家也会有走投无路、冒险一试的时候。
管轶回忆,当时韦伯斯特对他说:“我比较老一点。……如果明天我出了什么事,你可以继续做研究。”
上世纪70年代,当管轶还是江西宁都县的一名贫家少年时,吃鸡对他而言是件极为难得的事。一有这样的机会,一家人总是从鸡头鸡爪鸡肉吃到内脏:一只活鸡去毛烹煮后,能够吃上好几顿。
44岁的管轶现在是研究禽流感病毒的专家,十多年来一直与活禽和野鸟打交道,可他却再不敢享用家禽的内脏。与普通人一样,他也常会因为不可预知而产生畏惧:昔日活蹦乱跳的美味,会不会蕴藏着危险?
1997年,香港暴发了禽流感,大量家禽因为感染一种名叫H5N1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而死亡。H5N1也就在这一年引起管轶的重视,之后,他花了几乎十年的时间追踪它,却依然不能完全了解这种病毒。
管轶的办公室坐落在香港大学新建的医学院实验楼,窗外就是淡蓝色的大海。不过,他无心欣赏海景。他的脸色并不好,宽大的镜框遮掩不住眼中的焦虑。
“我总是处在悲惨世界之中。”他自嘲道。
管轶一直担心,阴魂不散的H5N1病毒某天会在动物间暴发、偶尔感染人类,然后变异成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大流感病毒。
历史上,人类曾经出现三次著名的大流感。1918年,著名的西班牙流感,导致欧美5000万人死去;第二次是1957年至1967年全球范围的流感;1968年“香港病毒”也引起了一次大流感。而在许多科学家眼里,目前禽流感蔓延的情况,很可能引发新世纪第一次全球性大流感。
H5N1已经在多个冬春反复肆虐,今年更蔓延到了欧洲,以及最贫穷、防护能力最弱的非洲。仅在中国,包括4月18日湖北省确诊的最新一例在内,迄今已出现了17例人禽流感病例,其中11名患者死亡。
作为香港大学微生物学副教授和国际动物流感学界的权威,管轶第一次为全球瞩目,是参与首先发现并证实SARS冠状病毒是“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钟南山当时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
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18名医疗英雄之一,但他并不稀罕这些虚名。他是那种手脚勤奋、笃信科学研究规则、有时又直率得令人讨厌的人。“我们都不是先知。”他经常自谦道。
这些年,他主持的港大流感研究中心已从样本中排出了数百个H5N1禽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而目前世界上所有的20多种H5N1禽流感变异类型,也由其实验室鉴定出。
但他从未因此特别高兴过。因为病毒变异得越快,种系越多,应对之策略就越难奏效,人类面临的危机,只会更多更重。
发现H5N1
1997年冬,香港暴发禽流感。管轶的博士生导师罗伯特·韦伯斯特从美国孟斐斯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实验室(世界上惟一研究流感在人畜之间交互传染的中心实验室)赶来,拿着简易赶制的禽流感疫苗试剂,准备把它滴进自己的鼻孔里。“我比较老,所以我先来。”韦伯斯特说。
这样就能使人体获得对H5N1的免疫能力吗?当时,科学家们对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病毒还没有多少了解,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次尝试。
“疯子的行为。”管轶形容。但科学家也会有走投无路、冒险一试的时候。管轶回忆,当时韦伯斯特对他说:“我比较老一点。……如果明天我出了什么事,你可以继续做研究。”然后,这个老人不忘与管轶约定,如果他第二天还健康,那就轮到管轶把试剂滴到自己的鼻孔里——就像俄罗斯轮盘一样,这样的危险谁都得去面对一次。
作为一个标准的“滤过性病原体学者”(《Science》,2006年3月3日号),当时管轶的脑袋里有无数疑问:
H5N1从哪里来?
它是怎样产生的?
它的家族有多大?
它会变异吗?
它是怎样在家禽里传播的?
……
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答。因为首先要找到它们。
“秘密警察”
对比起当年的“走投无路”,现在科学家们对禽流感病毒的认识比当年深入得多,研究行为也系统得多。譬如,管轶已经知道,禽流感很大程度上是禽鸟的肠胃病,病毒会大量分布在病鸟的消化系统里。
但H5N1病毒并不像森林里的老虎那样清晰可寻,它们往往在某地的禽鸟里突然肆虐,又转向另一个地方,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让追踪者们疲于奔命。
“我就像一个秘密警察一样。”管轶说。到市场里捡禽鸟的粪便,成为他主持的港大流感研究中心最日常的工作之一。
港大流感研究中心同时也是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部,2004年挂牌)。在这里受雇的港大医学院研究生,会定期到香港社区的活禽档口,用一些比小指头还要小的棉签,把鸡鸭鹅的粪便,小心翼翼地放进小试管里。
这些小小的、肮脏的工作,往往能发现很大的问题。管轶记得,1997年H5N1在香港导致18人感染,其中6人死亡。当时他们在农贸市场大量抽取活禽鸟的粪便样本,发现H5N1带病毒率竟高达20%。
香港有二三十个禽类市场,两三千个档口,每天消耗的鸡是十几万。“弹丸之地,人和鸡挤在一起,难免有人中招。”
管轶和气温婉的太太,亦是港大流感研究中心的雇员,也要和管轶轮流到市场去取样。“香港特区政府支持我们做这些研究,所以总有市场管理人员带着到档口去,不然很多档主都不会让我们取样,因为这显然会妨碍他们的生意。”她说,除非内地、香港有大疫情,她才会亲自和丈夫一起,跑到疫区现场取样。
2000年开始,管轶走出香港,开始繁复枯燥、大海捞针般地在中国东南部各种禽鸟市场里的寻找。他和他的太太,以及同事在东南部6个省份的家禽集散市场逐个逐期取样,样本超过了5万个。
以下是样本来到管轶实验室后的基本情况——
大多数情况下,从市场里取得的样本,还未确定是否带有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病毒,它们将在P2实验室里被彻底调查:
那些事先被消毒过、用来取粪便样本的小棉签,被插到小小的试管里面,以特别的药水去菌,成为只可能培养出禽流感病毒的溶液。然后,它会被研究人员种到鸡蛋的鸡胚里,潜伏的病毒如果在鸡胚里繁殖,就会被人们发现。
当某个鸡胚被发现有病毒时,他们就会检验,到底H和N是什么亚型。
很多时候,这些鸡胚里检测到的只是H2与H9或其他低致病性病毒,偶尔也会有H5。这会让大家“兴奋”——某种意义上也是忧虑,尤其是当病毒在一个新的地区被发现。
通过大量的抽样调查,管轶发现在华南的家禽里,活鸡并不是H5N1最大的载体群,鹅与鸭比鸡带毒几率要大得多。“家鸭1.8%,家鹅1.9%,鸡0.26%。”他在研究报告中说,直至目前,家鹅依然是100只里几乎有两只带毒。
长年累月寻找H5N1,对管最直接的影响,是再不食用家禽的内脏,尤其是广东的名菜:白灼鹅肠。鸡肉他仍然会吃,但他会把切好的禽鸟用自来水冲上1分钟。他也不住地对自己、家人、也对朋友强调:必须要彻底煮熟。必须。
“鸭子才是最危险的。”
管轶把病毒标本带回实验室“解剖”、画图后,发现它们与南方家禽所带的H5N1,竟然是后辈与前辈的关系。
候鸟有多少罪
2002年10月初,冬天即将来临,候鸟开始从西伯利亚的寒冷地带迁向温暖的南方。管轶江西老家北部的鄱阳湖,就是候鸟在中国的三大栖息地之一,不时有群鸟在这个温暖的淡水湿地上飞起飞落,安静而欢快。
这些鸟儿身上有H5N1吗?在欧洲,H5N1的踪迹并不多在家禽中发现,而是在天鹅等候鸟的尸体上被分离出。迁徙的鸟儿每年冬春都会在全球各大洲间飞行,这给异域带来了危险。
这是管轶夫妇以及科研人员们第一次来到内地候鸟栖息地与野鸟接触。他们在湖畔寻找候鸟的排泄物,或直接捕捉一些候鸟,以获取它们的血液样本。尽管这比在市场里捡粪要耗费更多的体力,但他们不需要看家禽贩子、农场主和管理人员们的脸色。
从那时起到2005年,每年冬春,管轶都会在此等候候鸟。他最想知道的是,候鸟在H5N1的传播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科学家们对禽流感的流行究竟主要是因为家禽的养殖、贸易,还是候鸟的迁徙始终争论不休,追踪家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管轶试图从候鸟入手,从另一个侧面进行了解。
但科学研究往往会超出预想。
从2002年的冬天起,管轶的团队在鄱阳湖和香港的湿地湖泊收集了超过1.3万份候鸟/野鸟的泄殖腔腺与排泄物样本;在总共1092只迁徙野鸭的血清学样本里发现有3.1%初步感染了H5N1;2005年,他吃惊地发现,在鄱阳湖,6只“看起来显然很健康的野鸭”身上居然分离出H5N1病毒。
“鸭子才是最危险的。”这成为他后来常挂在嘴边的话之一。把病毒标本带回实验室“解剖”、画图后,管轶发现它们与南方家禽所带的H5N1竟然是后辈与前辈的关系。究竟野鸭跟家鸭是怎么发生接触,病毒又是怎么从后者传到前者的?是野鸭跑到运输家鸭的笼子旁边?是它们在养殖场里有了亲密接触?还是某个鸭子的粪便掉到了野鸭头上?……管轶无法想象这个过程,这是“复杂而不可能一步步推敲的”。
谁是H5N1家族的“爷爷”?
不能一网尽收,但管轶必须继续与这些危险的小东西打交道。鸭子的行为无法琢磨,但不同地区病毒间的亲缘关系还是有办法解开。
一旦收集到的样本中发现有H5的踪影,这些样本就会和那些“高度危险”的样本(譬如从已知有大量禽鸟死亡的地区带来的样本)一起,直接进入多道厚厚金属门封锁下的P3实验室,等待进一步处理。
“我们会把病毒灭活,‘砍手砍脚’,把内脏拿出来。”年轻的香港女孩Carmen刚在香港大学传染病学系完成硕士学位课程,现受雇于管的实验室,任务是给病毒们的基因“画图”。画图前,同事们会把病毒基因里的DNA和RNA抽取出来,然后放大、照相,在电脑里描绘出具体的序列构成。
H5N1的结构远比人类要简单,在那表面长满小刺的球状病毒里,只有8根基因,但它们变异的速度比人类快得多。在Carmen的电脑里,病毒的基因图是一张类似心电图的长条波型图,不同的病毒基因图放在一起,就可以逐段进行比较。“这是为了发现病毒间的亲缘关系,就如同警察们侦查AIDS从谁传染给谁一样。”
管轶最让人尊敬的地方,是他长期在华南、东南亚这些禽流感高发的区坚持大量取样,因此他能够研究的病毒样本足够的多,研究结论也呈现出足够的说服力。管轶曾为一些特定时期在特定家禽上分离到的“经典病毒”描绘出长长的家族树,这些树揭示了该地区H5N1在时空或地理上彼此间的亲缘关系,甚至可以联系到欧洲天鹅身上禽流感病毒的起源。
在管轶展示给全世界的几份论文里,1996年的广东鹅(里分离出的禽流感病毒)是“爷爷的爷爷”,标在家族树的根部。管轶还发现,H5N1病毒在东南亚很可能已经成为了地区病,在特定的区域里呈现着特定的基因特性。
港大流感研究中心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确定的8个参比实验室之一。8个实验室的科学家们都可以共享各自最新的发现,看看彼此找到的病毒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追踪病毒们变异的线路。中国内地、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地的病毒样本,不断地被送到香港流感研究中心。
管轶的电子信箱也会每天收到以几页计的邮件,大多是其他世卫实验室为亚洲、欧洲、非洲等地区分离出的流感病毒的病毒分离情况、感染情况、暴发情况、分子结构定性分析、来源分析等。
在欧洲相继暴发H5N1禽流感后,通过世卫8个实验室的共享资源,综合过去对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研究,今年2月,管轶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上描绘出亚洲H5N1们的变异关系。
“……我们国家,云南,03(指2003年发现,下同)、04、05在这里;……越南,03、04、05在这里,跑不掉吧?青海湖的在这里对不对?青海湖之前的江西的在这里对不对?在鄱阳湖就找到它了……这是爸爸,这是儿子……”管轶快速、肯定地指着H5N1图谱的各个颜色和符号,一遍遍激动地阐述。“我们经过大量的围堵,才能知道来龙去脉,它(H5N1)的每个基因都被我们搞定了。”
这是管轶多年对H5N1探索的系统性结论之一,也是对世界传媒有极大影响力的研究结果。他总是为此激动,一方面因为这是建立在超过十年、超过十万个样本研究之上的结论,当然,它又引来了诸多争议,为此他不得不一次次解释。
太多不可预知的问题
发表在国际顶级科学杂志上的这些结论到底是解释性的,它一直没有对管轶最关心的问题——对家禽采取措施——起作用。
管轶曾经向舆论表达过对家禽养殖业的质疑。他认为,超过6成的散养模式无法使鸡鸭鹅避免与其它禽鸟产生交叉传染,而面对变异频繁的H5N1,用在家禽身上的动物疫苗也未必能完全奏效。
同样的一些观点也来自中国农业部。4月初,农业部国家首席兽医官贾幼陵说,大量候鸟北迁,春季家禽大量补栏,长途贩运增多,偏远山区散养家禽疫苗接种不规范,这些因素使我国禽流感防控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争论还在持续,而管轶还有更多的问题要想。有些是被人反复追问的,比如,禽流感病毒会在人类引发大流行吗?
目前,全球已有45个国家发现有禽类感染H5N1型禽流感病毒的病例;在195名人类患者中,已有半数不治身亡。
“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办公室里,管轶不断地踱来踱去,大声打电话,兴冲冲地与内地的科学家谈话,相约在发现有人类感染禽流感时,立刻一起到现场培养活体病毒标本。
“人对禽流感病毒是非常不敏感的,甚至应该说不可能——现在是从不可能里发现了可能——人类还有禽流感病毒不完全了解的缺陷。”说到这个问题时,管轶的声音缓了下来,慢慢沉了下去。面前摆着他朝夕相处的H5N1病毒模型,圆溜溜的,比他的头还要大。
已有科学家开始在这个“万一”的问题上发表结论。2005年年末,美国军事病理研究所的病理学家杰弗瑞·陶本伯杰发表文章,认为1918年西班牙流感H1N1病毒,其实是禽流感病毒的一种类型。管轶认为,他的研究混淆了人类流感和禽流感,最后必定无法自圆其说。在希腊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上,管轶不管彼此之间良好的关系,非常认真地与陶本伯杰讨论:“你能这样下结论吗?”
管轶说自己是一个太老实的人,在旁人眼里则是太直率。在他的言论里,经常用到的是“不确定”、“可能”等字眼,而不是世界领先、第一、阶段性胜利等词。
“譬如我说禽流感不会一下子消失。”管轶清晰地记得,2月6号下午6点40分,他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发表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报告之前,认真地向国务院科技部提交一份报告,里面列明了他一再申明的调查结论:
H5N1禽流感病毒一直没有被消灭或有效控制。
看起来健康的家禽样本中分离出H5N1禽流感病毒。
鸭和鹅等水家禽比鸡带H5N1禽流感病毒的几率要高得多。
内地H5N1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个案与活禽市场可能有密切关系。
……
在预防禽流感的征途中,管轶认为自己每一步都向中央提供了建议和参考。“知道多少就告诉政府多少。由政府来决定。国家利益在先。”
即使是讲述他的世界禽流感病毒图谱,管轶也是一脸的焦虑与激动。他似乎总是不懂得笑。这个潜心于研究病毒间父子爷孙关系的人,只有在讲起儿子时脸上才会流露出轻松自然的笑容。“我快要当爷爷了。儿子今年上大学了,我还不是快要当爷爷了吗?”读生物的小管,也像候鸟一样,幼年在美国,长大在香港,现在又飞回了美国读大学。
当然,管轶本身就是一个飞行物体,早年时成百上千次出没在华南的市场和湖泊,现在则忙于四处合作、出席会议。他每天只休息6个小时,其他时间都被安排到以半小时为单位的工作时间表上。
4月4日,穿过多扇厚重的金属门,穿过整个封闭严密的港大流感研究中心区域,管轶跟他胖乎乎的博士后助手,来自澳洲的Gavin Smith,以近乎教学一般的语调用英语交流了几句,然后告诉记者,从办公室可以远远地眺望到自己的住处。那是更接近大海的地方。他打开一扇玻璃窗,在戒烟糖旁边抽起了烟,然后叉起腰轻声说:“那就是我的家。”
链接
5中国政府防治禽流感的四大措施:
对禽流感地区的家禽进行大规模扑杀;
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同时实施广泛的疫苗注射;
采取措施,防止禽流感向人传播;
同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及时通报情况。
5中国关于禽流感防治的相关条文
2005年11月21日,我国对外发布《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该条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的形式发布,成为目前我国应对重大动物疫情的最新法规。
与11月1日由农业部公布的《农业部2005年秋冬季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实施方案》相比,该条例对疫情上报条件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一只要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死亡的,就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的县(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而后者经现场调查,如果初步认为属于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逐级上报。
2006年4月,正是候鸟北迁的季节,也是禽流感等各种动物疫病高发季节。为落实国务院提出的“逐步实行全面免疫”的政策,农业部制定了《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行动工作方案》和《2006年春季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意见》,突出强调了免疫工作。今年中央财政将拿出8亿元,地方财政配套9亿多元,用于禽流感、口蹄疫疫苗的供应。
中国北京
四月,候鸟的翅膀扇动人的神经
天气转暖,自由的鸟儿又开始大举北迁。这些候鸟具体从哪里来到哪去,这些候鸟是否会携带禽流感病毒。于是,人们也就开始绷紧了神经,开始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目光已经无法离开这些鸟儿。
大批的候鸟又要到北京过春了,张铁楼的神经又该绷紧了。“加班加点啊,已经习惯了,”张是北京市园林局严防候鸟传播禽流感领导小组办公室高级工程师。去年10月份,张铁楼参与到严防禽流感小组的工作,此前他一直在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负责组建基地。
其领导小组的一项工作是每天接收各个监测站上报来的情况,统计汇总后再上报给北京市防治重大动物疫情指挥部和国家林业局。这项工作由张铁楼亲自负责。
据记者了解,为了应付春季候鸟的大批迁徙,北京的监测站已经达到了102个,“这些监测点基本上可以覆盖全北京,不留一个死角。”而全国范围内国家级和省级监测站点已经达到550多个。
忙碌已经成为常态
张铁楼上周六在办公室值班。本周内,他有4天是在北京的各个郊区考察。
每天下午4点钟,各监测站将当天的监测情况列表上报,这些情况包括站点鸟群的种类、数量,以及有无疫情等。目前,北京将鸟群分为雁鸭类、鸻鹬类、鹭类、小鸟类、猛禽类。张铁楼说,当前国际上认为水禽禽流感更难防控,因此监测站重点关注的首选水禽。记者从农业部了解到,水禽尤其是鸭是流感病毒巨大的贮存库,其病毒能以高滴度从粪便中排出而污染水域及其饲养场所。而水禽与鸡混养的情况也导致水禽流感病毒极易传染给鸡等陆生禽类。
4月4日,下午4点钟之后,张铁楼开始陆续收到各监测点传来的报表。在所有报表都收齐后,张铁楼对情况做了一番简单的分析,然后做出一份“候鸟监测情况日报”,并附有“北京市鸟类监测日报明细表”和“监测日报表汇总”,这些材料要在下午5点钟一并上报到北京市防治重大动物疫情指挥部。记者在这份日报上看到,当天本市各监测站(点)共监测到雁鸭类11129只、鸻鹬类80只、鹭类37只、小鸟类20846只、猛禽9只,总计32101只。截至今日17:00没有发生鸟类疫情。
小杨是某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他目前正在严防候鸟传播禽流感领导小组办公室实习。在下午4点到5点的时间里,小杨一直守在办公室里那台传真机前,各地传真像战报一样源源而来。不过最基层监测点的情况首先汇总到区县级的监测站,由他们整理统计后再传到领导小组,因此最后传到张铁楼这里的报告大约有40多份。
要将这些材料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整理完毕,也不是件轻松的事。但张铁楼说,这还算是好的,去年10月、11月候鸟迁徙高峰的时候,领导小组的工作人员几乎是24小时值班。眼下又到了候鸟迁徙的另一个高峰,所有人又绷紧了神经。
第二天的上午11点,这些材料还要再上报给国家林业局一次。通过这样的层层上报,一方面可以即时掌握北京的鸟类监测情况,另一方面也为不同部门间的合作做了准备。
据了解,北京的监测站点是经过专家严密论证后确立的。在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幅候鸟监测站点分布图。张铁楼指着分布图告诉记者,郊区的站点主要根据北京的水系确立,北部有白河、汤河、潮河,共同汇入密云水库,往南是温榆河,再接下来是拒马河,沿这些水系不同地段都有市区两级监测站,加上大型水库、湿地山区、市内公园等,基本上能够覆盖整个北京。
在这些监测站点,有近4万名专、兼职人员在进行鸟类监测。他们在上岗前,都经过领导小组的专门培训。由于这些观察员原来都是各地的林果技术员、园林工作人员,他们对监测点的情况十分熟悉,因此工作很快就进入轨道。
观察员们每天走在自己负责的区域内,如果发现有鸟类异常,比如出现病鸟、死鸟,立即同时报给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当地疫情指挥部,然后请来当地兽医部门进行检验,确定原因后再决定处理方式。
一个监测点的观察员
张铁楼说,目前北京每天监测到的候鸟、流鸟总数达到3万多只,分布在100多个监测点。在上报给张铁楼处的各类报表中,玉渊潭公园候鸟监测点观察员宋建民的报表内容也在其中。在北京,有100多个这样的监测点的报表直接或者经过一次汇总后上报给张铁楼。
4月6日,早上8点半。宋建民准备开始一天的观测,他带的工具是一个望远镜和一本文件夹,里面有记录情况用的表格,此外,宋建民还自备了一个小照相机。
此时正值玉渊潭的樱花节,早樱缤纷,如堆雪砌玉。每年这个时候,也是鸟儿大批来到玉渊潭的时候。
作为一个水面广阔的公园,玉渊潭被确定为北京四个市区内的市级监测点之一。
宋建民2004年成为这里的观察员,此前他一直在公园内从事园林绿化防护工作。在上岗前,宋建民接受了园林局的两次培训,主要是学习如何分辨鸟类异常,如何填报统计表格。宋建民说,他自小就在玉渊潭附近长大,后来又在园子里工作,对这儿的鸟类也不算陌生。在培训班上,宋建民了解了怎么给鸟类分类,如鸣禽、猛禽、水禽等,每种鸟的名称、习性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知道鸟类如果感染了禽流感是什么症状,“口中有黏液,腿下有出血点,脖子向后仰,站立不稳,这些都是异常症状,发现了就要立即报告”,宋建民说。
培训班有时讲的不够仔细,光看图片和资料也没什么印象,宋建民就找到鸟贩子取经。前两年北京还没有取消活禽交易的时候,鸟贩子那里聚集了各种鸟儿,宋建民认识了红子、背儿、粉眼儿、红靛、蓝靛等鸟类。鸟贩子还告诉他什么鸟叫什么声音,光听声儿就能知道有多少种鸟儿。现在,宋建民说他虽不是所有鸟都了如指掌,但也能看个差不多了。
每天早上8点半,宋建民开始观测,到下午2点钟,一天的观测基本上就完成了。随后,宋建民回到办公室填写统计表。
在玉渊潭,宋建民顺着樱花园的路直接到西面的湖,然后拿出望远镜来看,这样扫一圈,附近有多少鸟儿就已经知道了。宋建民说,玉渊潭的鸟儿每天有900只左右,最多的是鸣禽,约有700只,此外,雁鸭类有近100只,鹭类、猛禽等也有近100只。“天天来看,数量差不多,今天多一只明天少一只,基本上很快就能发现了。”
在留春园,宋建民观察得特别仔细,他说这里是玉渊潭的重点区,所有来的鸟儿都会先在这里聚集。这时,一个游人告诉宋建民,那边的水面上来了一只鸭子,是新来的。昨天都还没发现。
“这些游人都很热心,有鸭子不吃食了,他们都会来报告我。”宋建民在培训班上知道什么情况要格外注意,比如鸟儿生病了、竖毛了,或者赶不走,都属于异常,要赶快上报。
有一次一个游人告诉他有只鸟趴在水边,一动也不动,他听后立即赶过去,没想到保安不认识他,愣是不让他去,宋建民怎么说都没用。后来他朝对面大喊一声,趁着保安回头看,宋建民就溜过去了。到了那儿发现鸟儿闭着眼睛,宋建民捡起一块石头扔过去,鸟儿忽然扑拉拉飞起来了,原来是虚惊一场。
宋建民工作很仔细,记者在他的记录表上看到,需要填报的内容包括每种鸟类的数量和有无异常,但宋建民自己还做了一个表,记录鸟类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同的数目。
一个半小时下来,宋建民转了公园的北边一半,接下来还要再去南边。“一天下来,要走上20里地”。宋建民还给自己的工作总结了四个字,数、听、观、望。数鸟类的数目,听鸟儿的叫声,观察鸟儿的觅食活动情况,再从整体望鸟群有无明显变化,通过这些办法,宋建民把玉渊潭公园的鸟都记了个结结实实。
候鸟从哪来到哪去
张铁楼目前比较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候鸟的迁徙规律,包括鸟群迁徙的路线、时间、觅食地、停歇地等。他认为,研究候鸟迁徙规律的工作是基础性的,可以为鸟类的监测提供更科学的依据。从目前来看,根据鸟类环志来推算鸟儿的迁徙路线是非常有效的办法。
也正因为如此,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眼下正处于最忙碌的时候。环志中心主任楚国忠3月底刚刚从青海回来,他在青海湖的鸟岛上负责卫星监控候鸟迁徙路线项目。去年5月份,青海湖发生禽流感,短短20多天的时间里,造成1000多只候鸟死亡。到去年6月底,死亡鸟数超过了6000只。去年7月1日,农业部兽医工作新闻发言人、国家首席兽医师贾幼陵宣布,青海候鸟禽流感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
今年3月23日,卫星监控候鸟迁徙路线项目在青海湖启动。楚国忠介绍,这个投资300万元的项目由国家科技部主管,。所谓卫星监控,就是在鸟儿身上安装一个卫星信号发射器,然后用租用的法国卫星接收信号。楚国忠说,这是当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候鸟跟踪监测技术。
根据已知的研究结果,世界上共有8条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其中3条迁徙通道都与我国候鸟迁徙有密切关系,基本覆盖了我国全部国土。候鸟在中国的迁徙路线从东到西可分为3条:东部是从东北到东部沿海,中部是从内蒙古到中部湖北、四川等地,西部则是从西北到青藏高原。
楚国忠带领的项目小组现在正集中精力研究鸟群的迁徙路线,“也就是越冬鸟的来龙去脉。”楚国忠说,现在已知的迁徙路线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鸟类具体从什么地方来,在哪里停歇,这些现在还弄不清楚。据楚国忠介绍,现在全国只有20多个环志站,而以我国如此大的地域,要达到三百到五百个才能有效地回收到候鸟的环志,从而推知它们的路线。楚国忠说,比如去年引发青海湖禽流感的斑头雁,曾在印度北部回收到,现在可以大致推知其迁徙路线。9月份斑头雁向南迁徙到缅甸,沿着中亚、印度迁徙通道,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西藏,到达印度北部过冬,次年4月份再返回青海。
楚国忠告诉记者,多数鸟类的迁徙路线现在还不明了,而卫星监控的项目启动后,估计到明年春季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出来。获知鸟类的迁徙路线之后,对疫情的预警系统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了。这是楚国忠希望达到的目标。
除了在青海湖的工作,楚国忠也会与国外同行进行一些交流。鸟类环志是世界性的,目前与我国沟通较多的有日本、韩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来到青海湖的鸟儿里有一些就是从这些地方来或者经过此地。
德国马尔堡
病毒专家成了公众明星
“儿子都抱怨说,我快成公众明星了”,德国马尔堡大学病毒研究所所长、国际知名流感病毒专家、Hans-Dieter. Klenk教授(下称Klenk)笑着说,由于禽流感的扩散和威胁与日俱增,如今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之外,他更是成了媒体的抢手人物,即使是普通的德国民众,也会纷纷把电话打到研究所,询问有关情况,教授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自然大大缩短。
自从有了禽流感的报道,很多人不敢吃鸡蛋、鸡肉。前些天有海外媒体还报道说,来自疫区的牡蛎也建议不要食用。当记者告知Klenk教授,德国发生禽流感以来,德国今年3月份的禽肉类消费额降低了1.5亿欧元时,教授称此举不足取,“我自己就是家禽消费者。”和很多病毒研究学者一样,Klenk教授认为,经过高温烹制,民众的食品安全是可以保障的。
教授明星子承父业
与德国其他大学一样,马尔堡大学的100多个院所散布在城市各处。从马尔堡中心火车站,搭乘7路汽车,可直达马尔堡大学的生物医药研究中心区。Klenk教授所在的病毒研究所也是去年年底才迁入该区域。
Klenk教授的办公室在中心大楼另一侧的建筑物内,房门上标的号码是+1/63591。今年68岁的Klenk出生在西部名城科隆。也许很多人知道Klenk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流感病毒研究专家,却不太知道正是教授的父亲、生化学家Ernst Klenk,1940年发现了H5N1病毒中“N”所代表的神经氨基酸酶蛋白(Neuraminidase)。
Klenk教授今年3月份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对于禽流感病毒的了解还处于起步阶段”。一个月后,他告诉记者,针对禽流感,研究所现在主要的工作是通过基因研究,对流感病毒在哺乳动物间的跳跃传播进行研究。此前,Klenk教授和同事们通过动物试验发现,如果病毒得以迅速复制,那就表明蛋白质发生异变,从而使流感病毒得以跨越种群限制。
至于世人担心的人传人的禽流感变异,Klenk教授的回答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出现了人群间传播的病毒变异。”或者说,至少现在没有确认人—人传播的传染链。
除了在实验室中寻求解决之道,Klenk教授还在各种场合表达其对禽流感防控的观点。
在像Klenk教授等专家以及政府的努力下,德国的防治措施颇为详细,现在妇孺都清楚直接接触禽鸟的危险。而自从发现猫感染禽流感病毒后,德国有关方面规定,携带家养动物(主要是犬类)室外散步时,主人不能解开牵绳,不能任其在室外游逛,否则要责罚宠物主人。
习惯同危险打交道
也许2007年会是Klenk教授和他的研究所收获的一年,因为投资1千万欧元建设的S4实验室,也就是最高安全标准的病毒实验室预计将在马尔堡投入使用,这也是Klenk教授多年的宿愿。目前的欧洲,只有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以及法国的里昂建有S4安全标准的实验室。
Klenk教授表示,出于科研目的,应当对危险病毒的遗传基因加以改变,但现在的实验条件不允许,“这使得很多现代手段无法运用,”当然也包括对禽流感病毒的进一步研究。
同在研究所工作的尤根·斯特克博士认为,实验室建成后,将使得病毒基因复制成为可能,对基因变异的致命病毒研究成为可能。从而可以让更多的科学家共同参与研究工作,对取得的研究结果进行求证,推进病毒研究以及疫苗研制。
与致命病毒打交道久了,Klenk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环境:隔离,封闭,高防护。从1967年发现马尔堡病毒以来,一直如此。与无形敌人——病毒的交锋时刻都在进行着。两年前的SARS疫情,在第一个病例发现后的两个星期就发现了病毒源,马尔堡大学病毒所是其中功臣之一。
因为禽流感蔓延、公众对卫生情况的忧虑,教授以及他的同事们也担负了更紧迫和繁重的试验和工作。“现在的情况令人不安。”同在研究所工作的沃夫冈·加登教授担心存在H5N1全面侵犯人体脏器的可能性。但他目前还不清楚,H5N1还需要多少次变异,才能适合人体寄主。
与时间赛跑研制疫苗
说到国际间的交流,Klenk教授介绍说,目前他们与上海复旦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至于此前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抗击禽流感的经验,教授认为对于他国防控禽流感大有帮助。
据了解,马尔堡大学病毒研究所的研究重点是病毒感染领域,其中心又着落在人与动物间的病毒原转化研究。因此Klenk教授目前忙碌的工作,除了禽流感是重中之重以外,还包括一系列的动物病毒研究。
2005年11月18日,Klenk教授的研究所召集国际病毒专家开学术会议,与会的包括英、美、加拿大等国的专家,会后一致认定,禽流感病毒产生变异,实现人群间传播,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寻找到根本性的对抗方法是当务之急。
更有效也更经济的当然还应该是疫苗。流感病毒为了维持生存,病毒还需要两种蛋白,即H以及N。而有效的疫苗可以帮助免疫系统生成抗体,对付血凝素以及氨基酸酶蛋白。人们试图找到一种广泛适用的疫苗,可以对付所有的病毒变体,“但是这种疫苗并没有找到,”Klenk教授说。
全球规模的疫情暴发也许不会发生,也许就在明天。全球很多和Klenk教授一样的科学工作者在不断的摸索中前行,也在和时间赛跑。
美国波士顿
帮动物免疫的夫妇
穿过春光明媚而又热闹的校园,进入马萨诸塞大学动物疾病科学系的Paige实验楼时,欢乐和明媚顿时像被关在了门外。沿楼梯而上,偶尔会见到一两个研究生握着装有液体的试剂瓶从一个实验室飞快地跑到另一个实验室。
四楼系主任Samuel Black的办公室紧闭,透过窗户可见他正和一个学生讨论。隔壁的门半掩着,那是Cynthia Baldwin的办公室。同为动物疾病研究专家的Black和Baldwin是一对夫妻搭档。
Baldwin眼下是成立才一个多月的“美国动物疾病疫苗研究网”的负责人。这是一家由美国政府农业部(简称USDA)投资210万美元作为初建资金的机构。“我们将通过对抗体的研究,提高对一些动物疾病的辨别和治疗能力,比如疯牛病和禽流感。”Baldwin扼要介绍说。
疯牛病对美国而言并不陌生;而即便是在正常的年景,与流感有关的各种疾病一样每年会夺去3万多美国人的生命。
就在过去的几个月间,美国西部11个州还刚刚经历了一场犬流感。这个同样是由H和N组合的病毒,从马流感病毒变异而来,并迅速在狗与狗之间广为传播,并使人们日常的遛狗行为变成是一种冒险。
但禽流感病毒显然远比犬流感危险。不过,生活在马萨诸塞州西部优美的康涅狄格河边的大部分人,仍然未把禽流感当成一回事。对他们来说,那只是报纸和电视上发生的事。
民众的满不在乎,并未让密切监视禽流感的美国官方和科学家们放松警惕。正相反,在他们看来,一场致命性的禽流感很快会在美国暴发。4月是候鸟北迁的季节,禽流感病毒将会随着候鸟的迁徙从疫区带到其他地方,并传播给将于今年秋季向美国南部迁徙的其他鸟类。
3月,美国国务院专门设立了禽流感行动小组,开始了与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农业部、国土安全部、国防部以及国际开发署的密切合作。
研究动物疾病并未影响这对夫妇的饮食习惯。“我吃鸡肉和蛋,甚至是半生的鸡蛋。”Baldwin大笑说,她不会因为担心动物疾病而不在超市里买肉类食品。
在这对夫妇眼里,有关动物疾病的很多研究都着眼于与人类相关的角度,着眼于动物自身的研究并不充分。比如禽流感,从人类的角度看,它已经造成了恐慌;可从禽类的角度看,禽流感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
世卫
两位官员的环球日程
2006年4月2日,中国;5-12日,老挝、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13日,纽约联合国总部。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下称世卫)专家、联合国禽流感事务高级协调员戴维·纳巴罗博士(Dr.David Nabarro)过去两周的工作日程。
12天的时间里,他舟车劳顿,奔波在亚洲这五个出现禽流感疫情的国家之间,其间与各国负责禽流感事务的政府官员会谈、交换意见,召开了多个新闻发布会,还抽空回复了积压在信箱里的一大堆采访邮件。
4月17日,美国东部时间的下午四点,当记者的采访电话再次打入纳巴罗的办公室,一向说话缓慢且态度友好的他有些克制不住的激动:“很多问题我已在各国的记者会上说过了,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有很多日常的工作需要完成。一个小时后我还要做演讲。”他语气中透出一丝疲倦,“真的没法接受太多的采访了。”
当禽流感已经成为生活中必须时时接触的一个字眼时,纳巴罗的心情显然可以理解。尽管他不直接参与研发和具体工作,但作为禽流感事务的高级协调员,他必须时刻为这种普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病毒奔波。那是他的工作。特别是在这个关口,亚洲之行得到的信息仍然让他充满了忧虑。
缅甸至今已出现了100多起禽流感。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关于禽流感的知识非常薄弱,并且,无论是在实验室的检测还是其他技术设备方面,缅甸都缺乏应对禽流感疫情的能力。
这正是世界卫生组织最为担心的事。预防禽流感的系统中只要出现一个薄弱环节,将会使整个系统受到破坏,因为禽流感病毒并没有边界和政治的概念。同样令人沮丧的一个事实是,目前人类社会还未研制出一种完美的禽流感疫苗或者治疗药物。
不过,世界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等联合国机构已派出小组,对缅甸局势进行总体评估,力图帮助缅甸获取资金,购置必要设备和药品并对宰杀家禽的农户进行补偿。
当纳巴罗正在为即将进行的演讲准备时,在大西洋另一边的瑞士日内瓦,世卫也即将开始新的忙碌的一天。再过8个小时,由世卫传播顾问Gregory Hartl领衔的小组,将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开始每天9点例行的电视电话协调会议,和联合国禽流感系统协调中心共同更新世界各地禽流感暴发和防治的状况。
自从禽流感疫情出现之后,这种沟通和联系已经成为常态。他们会讨论和更新各地媒体之前的疫情报道情况,商量在即将到来的一天中所有预约的采访,应当如何应对媒体的各种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说,等等。
作为一个中立的、世界性的协调机构的新闻发言人,他们必须谨言慎行,对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
Gregory Hartl预定给各媒体的采访时间一般从午后一点开始,当然,这是日内瓦时间。“请问在今春暴发的禽流感中,欧洲地区首当其冲,那么世卫的态度和措施主要是什么?”“嗯,我……我没法评价这个问题。”“No,我们谈下一个问题吧。”这样的措辞始终贯穿在整个采访过程。Hartl字斟句酌,不时停顿或修改自己的言论。
电话中的Hartl始终是一个老成持重的新闻官,只有当谈及自己的儿女时,他的语气才会轻松一些。“我的儿子已经足够大了,所以我会把一些禽流感的防治常识告诉他,让他在平常的日子里自己注意。小女儿则还太小,因而我没法跟她解释这样一种错综复杂、认识还不全面的疾病,只好通过我们父母的力量阻止她接近生禽,包括鸟类。”
和分身乏术的纳巴罗一样,每天接受采访的间隙,Hartl也要阅读大量来自各地记者各种不同角度和想法的邮件。“这真的是一个累人的工作,从照片的索取到采访邀约,需求量巨大。”
Hartl不做实地调研。他所在的部门,更像是一个关于禽流感的情报汇总机构。大部分世卫工作者每天主要的任务,是和世卫组织在各地的办事处、各国卫生机构一起工作。世卫组织要求192个成员国制定多部门程序,以协调农业、兽医和公共卫生(以及根据国情认为适当的任何其他部门)服务机构的工作,便利交流实验室和流行病学数据。这些数据中的一部分,最后会抵达Hartl这里,而Hartl的部门会根据各国情况给出不同的建议,必要时作出预警。
“我们只能在火苗蔓延之前把它扼杀在摇篮里,这需要迅速的反应机制。”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规划部总监代表玛格丽特·陈女士说道。
“每个国家太不一样了,拥有完全不同的基础,不同的领导制度,因而采取完全不同的措施和步骤。我们希望也建议大家在不同的基础上建立不同的系统,对禽流感进行围追堵截。现在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完成了这个系统的建设,大部分都在进行过程中。”Hartl说。
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Hartl拒绝对禽流感的暴发作出预测。因为这其中的变量太多了,一个变量的微动,就会引起极大的“蝴蝶效应”。“我们很难说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禽流感会暴发,这是为什么我们花费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希望各国都能做好准备的原因。”
“可以得出结论的是,如果禽流感不能在源头上得到遏制,它的传播速度将非常快,与此前的非典型性肺炎不同,SARS需要与病源的密切接触,但是禽流感病毒只需要通过空气就能随处传播,而空气无处不在。而且流感病人的症状显现会有一个潜伏期,这样一来,任何关于旅行迁移方面的建议,甚至禁止入境都不能够阻拦病毒的蔓延。之前的禽流感全球性大暴发,都是在六到九个月的过程中就传遍了全球的。基于21世纪的频繁商务旅行和交流,这个过程只需三个月就能完成。”
——《WHO(世界卫生组织)急性事件沟通手册·禽流感篇》
记者 许十文 丁佳 香港、汕头、北京报道 特约记者 柯卉 屠海晶 赵莹 德国马尔堡、美国波士顿、纽约报道 邓永安 施彦斐 摄 美国夏威夷大学李进岚对此专题亦有贡献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
一周热点
- 2019-08-30中央下发铁令!19年限养令、禁养令撤销!19年玉米生产者补贴确定,即将下发!
- 2018-08-05智慧养猪驱动 ——首届中国智慧养猪产业实践峰会在京召开
- 2018-03-27双胞胎第三代教保料“健康三宝”掀起抢购狂潮:仅发布会当天销售突破5000吨!
- 2017-10-11双胞胎集团9月份销量再创新高,突破86万吨!
- 2018-04-092018饲料工业展览会展商名录
- 2018-10-26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关于发布《仔猪、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蛋鸡、肉鸡配合饲料》2项团体标准的通知
- 2015-11-02双胞胎集团推出“三胞胎”直销大猪场
- 2018-03-08全国猪场大咖将齐聚三亚与双胞胎集团共谋猪事
- 2017-11-20年销量突破900万吨,双胞胎再现王者风采!
- 2019-03-26来2019河北饲料峰会 见证行业发展风向标
